
我拉开横在墙角的皮箱,折腾出入冬后卷起搁置的夏装,拽出箱子网格夹层一只粉红色的,巴掌大小的布袋子,然后连同收拾好的洗漱用品一块带进了浴室。
在生了锈的梳妆台上放英文歌,调到手机一半音量,我闭了双眼,双手扶着头站在淋浴头下面,感受温暖像海浪般在身上蔓延开来,蒸汽附着在镜子上,但我清楚地知道这镜子面前的我,是赤裸的我,真正的我,不加掩饰的我。
而在我面前的,梳妆台上的粉红色的袋子里,装着我人生中第一个性器具(玩具)——跳蛋。
我常常在这样的时刻——用音乐、流水以及唱歌的声音来掩盖自己使用性器具(玩具)的时刻,愈发觉得自己堕入了欲望的深渊,它的震动传递到我的身上,生理上的反应如同第一次和心爱的人亲吻时,蔓延周身的酥麻。
每次“做”完以后,我都会抹去镜子上的水雾,双手交叉放在腋下,从中认真审视自己年轻的身体,水珠从小山丘般的白皙的胸部滑落,一路延伸到平坦的小腹,而后陷入黑色浓密的毛发中消失。
在这样的,宁静的,只有我一个人存在的时空里,我发觉自己是性感的,即使我在做一件或许为他人所不齿的事情。

真的不齿吗?
我始终认为性的释放不过是如同吃饭、上厕所同样简单的生理需求。
只是在人类在起源时,即将男女用于交媾的部位作为羞丑来遮蔽,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,科学文明虽进化超卓,而对于性的认识似乎却不甚了了。
说来也像笑谈,姑且我们就当做笑谈吧,毕竟在这个人类文明对性的包容得到了最大化的时代,性,仍无法作为正常的茶余饭后的谈资被摆在桌面上谈。

性欲望,似乎成了私密而为人不耻的情欲。
然而我从始至终,不为自己使用性器具(玩具)而感到羞赧。
寝室有六个姑娘,姑娘A与我们鲜少沟通,常常夜不归寝,常常被不同的车接走,这是隐秘的;
姑娘B则是明目张胆,在一次学校国际交流的Party上认识了某法国男,四目相对,当晚即有了肌肤之亲,后来被自己的男友知道,二人分手,但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是,B姑娘竟和已分手的男友达成了身体明文约定——“只做炮友,不再恋人”;
姑娘C和D则是胸中无物的晚熟姑娘,没谈过恋爱,对性这个字眼更是唯恐避之不及;
姑娘E则频繁换着男友,介于张扬与收敛间;
而我,谈过一次长久的恋爱,已经感受过身体的高潮带来的快感,作为一个年轻女人的欲望已经被勾起,分手后常常会感受到来自身体深处的空洞,我知道,那是荷尔蒙又在暴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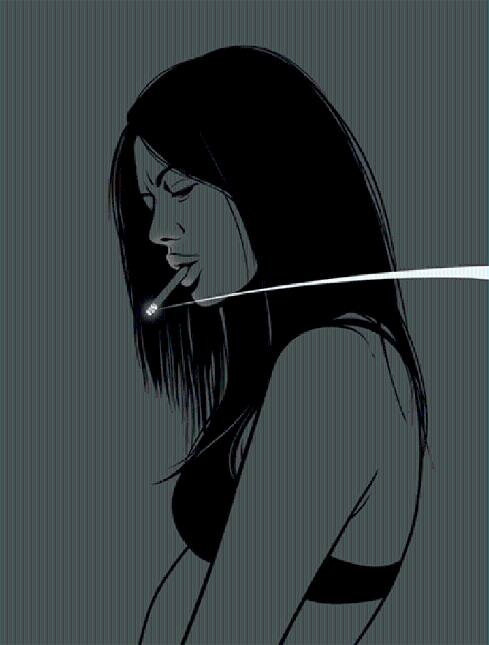
我怎么办呢?去约炮吗?把自己的身体当做物品与他人交换,获得欲望的宣泄吗?
我从未想过。即便我认为性是再普通不过的生理需求,却仍然坚定着不与不爱之人有肌肤之亲的基本原则,换句话说,我无法保证自己走肾不走心,我笃定身体是连接心灵的桥梁。
因此我选择了性器具(玩具)。对于性,我保持自己的底线,也因为有原则,才会内心磊落,没有挣扎。
所以,那些在深夜深处偷偷藏在被子里自慰的姑娘,不要再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多么羞耻的事情。
你没有以欲望为由而与不爱之人亲近,没有被欲望吞噬而失去了人应有的理智,你只是在不违背内心的前提下,满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,这永远没什么可羞愧的。
因为往往在这个时刻,你会真正感受到来自身体深处的一种美。

小赛语:每个人都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,少些道德评判,多些尊重包容